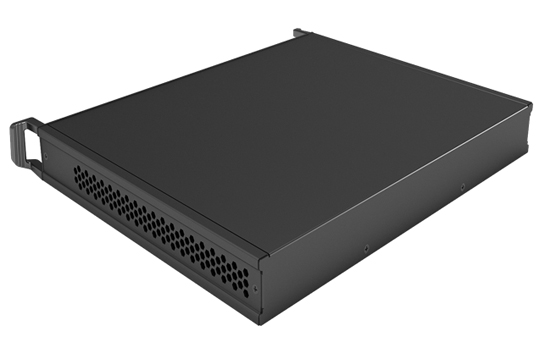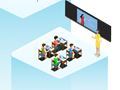山侖院士:我的根已經扎進黃土,拔出來會疼
http://www.wandqa.cn2025年04月03日 09:24教育裝備網
西吉、海原、固原曾被聯合國認定為“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”之一。如今,飛沙走石的“干沙灘”已經成了寸土寸金的“金沙灘”。在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的一封感謝信里,這樣寫道:“寧夏人民永遠不會忘記,20世紀80年代初,山侖等專家進入上黃村等地,做了大量開創性工作,使生產走上了良性循環的發展道路……”
山侖,“黃土高原上的昆侖山”。作為我國“旱地農業”的奠基人、作物生理學和作物栽培學專家、中國工程院院士,山侖是最早倡導加快我國旱地農業發展的專家之一,他主張將提高旱農生產力和改善旱區生態環境相結合,并成功地將旱農基礎性研究與應用技術加以銜接,形成了從基礎到應用的旱農技術體系,探索出了旱地農業良性生態體系的新路子。
山為姓,侖為名,這是來自我父母的祝福,他們希望我能以昆侖山的威武和黃土高原的雄壯為榜樣,頂天立地,為國家作貢獻。
1933年1月,我出生于山東省龍口市,父親在一家報關行當職員,母親是一名小學教師。
從我記事起,就是在母親“要好好學習”的教育中長大的。母親對孩子很嚴格,常常對我和哥哥強調“不受苦中苦,難成人上人”的觀念,她反對孩子們長大后從政或者經商,她認為,努力學習并掌握一門技術的人生更有意義和價值。母親十分愛國,讀過書,懂歷史,她常常給我們講1840年的鴉片戰爭,還有她崇拜的人物,比如孫中山、岳飛、林則徐等人的故事。
當年雖然國家動蕩,家庭經濟拮據,但是母親從未放松我們的學習,并始終激勵我們要發奮讀書、靠知識生存,是母親的堅持不懈,讓我最終進入了通往科學圣殿的大門。直到今天,我仍然倍感幸運和感恩。母親留給我的愛國、剛毅、正直、寬厚、忍耐、樂觀、上進等品德更成為我終身享用不盡的財富,使我在后來的學習和工作中能夠執著地堅持理想,勇敢地面對困難,能夠寬容地待人,公正地處事。
舊中國讓我感受到了生活的艱辛,但同時,中國人民表現出來的民族氣節,也更加堅定了我發奮讀書的決心,堅定了用所學知識報效祖國和人民的責任感。
童年和少年時期的我在學習方面并未表現出任何優于別人的天分,我記憶力一般,學習成績中等。上小學時,數學等作業常需哥哥輔導著完成,哥哥有時也難免抱怨:“你怎么這么笨呢!”我還記得有一次地理課上的畫圖作業,也因完成得不好被老師打回重做。
1950年夏天,我高中畢業,準備報考大學。父親不大贊成,因為按家里當時的經濟條件,供養兩個大學生存在困難。但一心想讓我們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的母親極力支持。最終,我考入設在青島的山東大學農學院農學系,成了新中國第一代大學生。
由于愛好文學,我起初有學文的意愿。但老師動員說:“要有出息就學一門技術。”受這種思想影響,我報了農學院。現在回想,報考的時候自己對學農并沒有什么確切的認識,似乎僅僅是出于一種親近大自然的心境吧。但誰能想到,這看似隨意的選擇,卻框定了我一生的選擇。
讀書時,我最喜歡的課程是植物生理學和土壤學,一是因為這兩門課的老師教得好,吸引人;二是我本身喜歡大自然,對植物生命活動規律、土壤中物質運動規律及其與環境的關系等內容充滿了興趣。因此,雖然這兩門課相對其他課程更復雜,但還是激發了我努力探究的欲望,所以成績很好。后來我選擇從事抗旱生理研究,到開辟出旱地農業生理生態新領域,其實都起源于大學時感興趣的這些專業課。
大學時,我的學習成績不錯,但實踐精神一般,一段時間里對上實驗課缺乏興趣。還記得一位負責實習的老師曾這樣對我說:“你在實習方面應當像在學習上一樣的好。”這句話,我記了一輩子。這個缺點,我也改了幾十年。
改正大學時的缺點,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道路,也是推動我后來事業成功的一個要素。我認為,科研能力必須通過實踐環節,在解決具體問題中提高。那些死記硬背的知識,不通過實踐,就不會轉變為較高的科研素質和能力。后來,我也是用幾十年的親身實踐,證實了實踐的不可替代性。
1954年8月,大學畢業后,帶著“服從黨的分配,哪里需要到哪里去”的革命熱情,帶著新中國第一代大學生的豪邁和激情,特別是母親的希冀,我來到了陜西楊凌,開始了扎根楊凌60多年的科研生涯。
還記得第一次來到黃土高原,老師帶我們在甘肅天水、定西、蘭州等黃土丘陵區調查,我震驚于那樣的廣種薄收、勞而無獲,痛心于那種燒草根、吃糠面的艱辛生活。
特別是在甘肅定西,我目睹了這一幕場景:農民跪在龜裂的田埂上祈求雨水,孩子捧著摻了草根的糠面糊糊。一位老農拉著我的手:“專家同志,咱這地真能長出糧食?”我喉嚨發緊,答不上話。
也就是從那時起,我看到了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和干旱問題的嚴峻,意識到了自己即將開始的這份科學事業的艱巨和重要。
20世紀70年代,我們去陜西安塞水土保持綜合試驗站的前身茶坊基點鍛煉,團隊擠在土炕上,每個炕都被擠得密不透風,翻個身要喊“一、二、三!”不然一個人難以完成,但就在這樣的條件下,我們工作熱情很高,干勁很大。雖然條件很艱苦,但在那個年代,一定程度上,艱苦已經成為幸運和自豪的組成部分。
1972年,聯合國糧食開發署將西海固定義為“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”之一。1979年,我受命擔任固原基點負責人,從安塞轉戰固原。這里也成為我全面開展旱農研究的現實根源,成為我的主戰場。我在這里總結出了糧食生產是自給性的、林業建設是保護性的、牧業生產是商品性的“三性”概念,明確了當地的自然與經濟優勢,肯定了固原縣農林牧業的地位與作用。這也是在黃土丘陵區農業建設目標上“三性”概念的首次公開提出。
1981年,我被任命為固原縣委副書記,也是中國科學院人員里最早被地方任命的科技副職。1982年,固原基點在上黃村建立了試驗示范區,這里生態經濟嚴重失調,資源環境的利用與保護呈現出尖銳矛盾,我們以生物措施為主,采取了一先行(草灌先行)、二側重(側重抓人工種草,側重抓旱作農業與化肥深施)、三同步(退耕種草、提高糧食單產和發展牧業同步)的技術路線,到了1985年,上黃試驗區林草覆蓋率達到70%,糧食單產提高91%,人均純收入達355元,比試驗區建立前提高了5倍多,農民捧著金燦燦的麥穗哭出聲來。
我們探索實踐的“上黃經驗”——“宜林荒山綠化,坡耕地梯田化,平川地高效集約化,不斷提高生態經濟效益,不斷提高農民科技意識和致富技能”,成為寧南山區生態治理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新途徑,受到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田紀云稱贊并要求在西部地區推廣。
在我看來,一輩子哪怕只干好一件事,就不辜負黨和人民對我的長期培養。20世紀80年代,我曾有三次離開楊凌去大城市工作的機會,我都放棄了,因為我覺得我的事業就在黃土高原,我的根已經扎進黃土了,拔出來會疼,我必須留下來深扎黃土,我舍不得離開。
20世紀90年代,當時有關旱地農業生理生態研究已經系統開展,但節水農業是當時國家的需求,我開始向節水農業研究方向轉移。我看到了水資源緊缺問題更有普遍性和重要意義,同時節水與抗旱本就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,于是我開始在多種場合,利用多種機會大力宣傳并倡導節水農業。
我的治學格言是“遵循科學道德,倡導科學精神:實踐——科學精神的基礎,創新——科學精神的本質,奉獻——科學精神的靈魂”。這是我在整個科研生涯中為自己樹立的一個標尺,也是我在后來培養學生過程中潛移默化灌輸的以“為人”為核心的“為學”之道。
不論對自己還是對學生,我一直注重“吃苦”教育,“不吃苦中苦,難為人上人”,這也是我自小從母親身上受到的啟蒙教育之一。我始終認為,吃苦精神是一個科研工作者應該具有的最基本的素質。
跟隨我時間最長的一名學生鄧西平,我安排他的第一件事,就是帶他去固原基點,七八個人擠在一張炕上,喝混著泥沙的窖水,吃泛著土腥味的清湯面,實地熟悉黃土丘陵區的地貌特征。還記得鄧西平第一次喝窖水后腹瀉了三天,我笑著說:“這水比蘇聯的伏特加烈多了!”
“博學”也是我一直注重的,我認為一個人一定要博覽群書,才能全面發展。在新知識、新技能面前,我始終把自己當成學生,不僅自己努力學習,也向有一技之長的人去學習,在我心里,有些領域,學生也是我的老師。
我們這批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生,主修的都是俄語,直到80年代才參加了英語培訓班但學得不好。后來我就自學,快50歲了還和青年人一起背單詞、聽錄音、練口語,硬是學會了。1987年的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,我第一次用英語主持了大會還作了報告,這激勵我繼續學習。1995年,在日本的一個國際會議上,我又用英語作了報告,會后也能自如地和國外專家交流。除了自學,我也時常向我的研究生請教,英語就這樣學了出來。我對計算機的學習也是同樣的,向年輕人學習,因為這些都是對工作有益的新鮮事物。
如今,回望科研歷程,我覺得以窮追不舍和持之以恒的精神追求目標很重要,這樣才能使自己的工作有系統性和連續性,雖然我遭受了很多挫折和困惑,但它們沒有擊敗我,因為我始終相信堅持正確的方向不動搖,是一個科研工作者應該具備的基本責任心和事業心,畢竟科研是個積累過程,中間難免遇到困難,所以能否看準目標堅持下來,是能否將研究做好的重要因素,堅持住是最重要的。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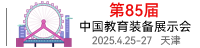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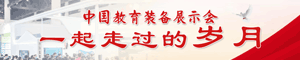






 首頁
首頁